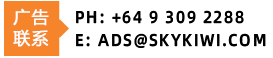与死刑犯谈话的人: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
日期:2020-07-21 10:04 阅读: 来源:长安剑
有人问,“为什么有些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,还要去找他们谈话?”
钱锦标会反问,“对身患绝症的病人,医生能见死不救么?”
钱锦标51岁了,他的家人、朋友,只知道他从部队转业后,成了杭州市看守所的一名警察,即使是他妻子,也从不知道他上班时具体在做什么。

在看守所工作15年,各个监区他都工作过。如今,他是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监管民警。他曾管教1000多人次的在押人员,日常最主要的工作是谈话,有时,一人一天就要谈五、六次。
10米高墙以内的监管,也许是警察这个行当里,最隐秘的角落,他们大多在阳光照不进的地方,一点一点等待冰川消融。
第六监区
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监区,是浙江省最早开创的艾滋病监管区,创立于2003年。
2014年,之前负责第六监区监管的民警老何即将退休。考虑到这个岗位的特殊性,所里动员全体民警,自愿报名接替老何,继续监管艾滋病关押区。
钱锦标主动报名,调入了第六监区。

与钱锦标之前所在的其他岗位不同,第六监区的全部在押人员,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。
他们不仅吸毒,牙齿发黑,还有人感染了梅毒,一旦毒瘾发作,会歇斯底里到抓破自己,甚至,身体溃烂、发臭、全身黑得像碳一样……
第一次走进六监区时,钱锦标也一样严严实实地戴上了口罩,但还是会觉得有一种本能的恶心,分分秒秒,都在抗拒。
他不敢多想,只是像以往一样照例巡监,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吃饭,有没有哪里不舒服,有没有情绪异常?他只是想,在押人员也是人,艾滋病在押人员也是人,慢慢去了解吧。
只要是艾滋病毒携带者,不论未决已决,都统一关押在第六监区。正因如此,第六监区内,也有死刑犯。
在押死刑犯的家人,在得知自己亲人被执行死刑后,来看守所领取遗物时,百感交集之余,都会小心翼翼去问一句,除了最后一次见面,之前,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话,哪怕一两句也行呢?
只要时间允许,钱锦标都会尽量详细地告知。
死刑犯的画
小马的毒瘾又犯了。
在监区巡视时,钱锦标见他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,不停抽搐着,好像是想噎死自己。
清清瘦瘦的小马,老家在四川,读书时成绩优异,但因为得了抑郁症,斗志全无。先是感染了艾滋,而后开始吸毒,没有钱买毒品,就假模假样地到杭州来,和家人说,杭州文化底蕴好,他来开古玩店。他真的有了一家小小的古玩店,只是一个壳子,实际是为了毒品交易。
当毒品交易无法满足他的日常,他自学制造毒品,并不断在多个临时住处售卖。被公安机关查获时,他正准备购买制造毒品的原材料,交易量超过500克,被法院判处死刑。
从2014年6月,到2019年,小马被关押在第六监区。期间,因身体原因多次保外就医,等身体好些,再回监区。钱锦标说,“考虑到这些在押人员的实际身体情况,为了增强免疫力,看守所每周有三天会加营养餐,内容有牛奶、苹果和鸡蛋。”可即便如此,还不到30岁的小马,依然羸弱。
大多数时刻,小马总是会想到要去死。第一次发现他这种想法,是钱锦标看了他写的悔过书,悔过书里他写——
“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,你快乐么?你是你自己么?或许,没有也许。”
钱锦标发现后,仔细观察他的进药情况,发现他都是把药夹在手指缝里,好像仰一下头咽下去,但都是悄悄扔在马桶。果然,小马在同监室的在押犯人熟睡后,悄悄把被单撕成白条,再搓成绳,企图上吊自杀。自杀行为被及时发现。
钱锦标找他谈话:“你还年轻,多争取立功赎罪。先不要把自己当成死刑犯,先把自己当作重刑犯。好好听医生话,能多和家人见几次。你父母始终是有牵挂的。有牵挂,他们也会努力活着。”小马不说好,也不说不好,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声气。
平时在监区,小马不太说话,但却人缘极好,主要是因为,小马画画好。在押人员说,即便在进来之前,也没认识过会画画的人。

小马(化名)的画。
“有时候毒瘾犯了,他坐立难安,给他纸和笔,他不停地写写画画,也就安静下来。而且,他画得极好。有时候,监区里也会为在押人员举办书画大赛,或黑板报大赛,他都会代表第六监区去比赛,都是拿前几名。”作为奖励,钱锦标会去看守所小卖部,买来方便面送小马。
但从画第一张画开始,小马便请求钱锦标不要把自己的画拿给家人,担心他们看了以后会更伤心,如果不嫌弃,就留给钱警官。
小马和钱锦标说:“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,我祝愿你长命百岁。”对于这些惜日如年的死刑犯,“长命百岁”也许是最深的祝福。
还是到了最后时刻,和家人见最后一面时,是钱锦标把他领到接待室的。“他父母亲都是四川当地老老实实的农民,得知儿子被关押在看守所后,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,又怕临时从四川赶过来,时间来不及,就在萧山的工地打零工。那天,他父母亲都赶来了,我在外面等着他们,大概有十多分钟,那个哭声啊,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小马父母亲来领遗物时,钱锦标依照小马托付,只转交给父母他们写来的信,还有小马那年从四川老家出来时,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全家福相片。
而小马的画 ,钱锦标至今保留在办公室。
一千只纸鹤
云南人小宏(化名),之前是保安,身形矫健,因为交友不慎,感染了艾滋,要吸毒,又没有钱,就想从卖淫女那里抢钱,卖淫女反抗,他心下一狠,掐死了卖淫女,被判处死刑。
被关押在第六监区以后,他依然凶狠,尤其是自己毒瘾发作时,经常殴打其他在押人员。有人被他殴打,钱锦标只能用手铐强制管理。
还有一些时刻,小宏对抗管教,不按时间作息,任凭钱锦标怎么叫他,他都用被子蒙上整个头。
钱锦标找他谈话:“你是睡不好么?和同监室的人相处不好么?你是对我有意见么?这样不说话,抵触抵抗下去,不利于解决问题,你不知道么?”
小宏或者一声不响,昂着头狠狠瞪着钱锦标,或者就很不耐烦回一句,“你不要啰嗦,你知道也没用。”回到监室,依然不断闹事。
钱锦标继续找他谈。“你为什么又蒙头睡觉?你为什么又不吃药?你为什么又不吃饭?你不讲事情经过,我就不知道,我不了解,就没法解决问题,你知道么?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。”
一直问到这一句,小宏才开口,说,“反正我是死罪。”
钱锦标说:“对待这种在押死刑犯,硬碰硬是没用的,他心里太狠了,如果有余温,那也只是缝隙。”有天,得知小宏牙痛,钱锦标请医生帮他找了药来,还帮他找了几本书,请同监室的室友一起打了热水,帮他洗了头。得知小宏的生日临近了,钱锦标向所里申请,从外面的蛋糕店买了一只蛋糕来。当小宏得知,这个蛋糕是专门为自己买的生日蛋糕,他从震惊到哽咽……
“这个滋味挺不好的,我自己老爸过生日,我都很少能回家,”钱锦标说,“我为死刑犯买蛋糕,不是对他们有感情,而是从监狱管理的角度考虑,要把所有的隐形矛盾,都提前消化。”
也是在谈话中,钱锦标了解到,小宏在云南老家有个未婚妻。知道他因强奸、杀人、吸毒关押在杭州看守所后,还写了信来。自从收到这封信后,小宏就开始沉默居多了。某一天,他对钱锦标说,他要纸,但不是画画的纸张,只要是能折纸的纸都可以,他要给自己在云南的未婚妻折纸鹤。

此后,小宏用钱警官帮他收集的纸张,大大小小折了一千多只纸鹤。这些纸张,是钱锦标陆续收集的超市促销纸和楼盘广告纸。小宏说:“等我死了,如果有个女人来看我,那肯定是我未婚妻,请钱管理千万帮我把我折的纸鹤,一个不少地交给她。”
小宏被执行死刑后,他的未婚妻果然来了。“我把这些纸鹤装在塑料袋里,最大的超市里的塑料袋,两只都装不下。我至今记得他未婚妻看到这些纸鹤时的神情,有震动,有唏嘘,也许,也有一丝丝原谅吧。”
第六监区最小的犯人1996年出生,只比钱锦标的女儿大两岁。钱锦标说:“我现在最大的愿望,就是我们监区不要再进来00后的在押人员了。”
人生中最长的十分钟
从高中起,钱锦标有记日记的习惯。
到看守所工作后,他有了两本日记,一本是工作笔记,一本是生活记录。工作笔记,写了18本。生活记录,写了6万字。
字迹是一个人的心电图。他写到自己的旅行计划,写到新疆、云南,就觉得笔记上的字也有几分潇洒驰骋。等写到管理心得,有种一蹴而就的迫切。

在看守所工作,又像老师,又像医生,又像足球场的守门员,面对的都是“疑难杂症”。钱锦标说,这是一份良心活,不是计件工种,是水滴石穿的活儿。
2014年6月,他刚到第六监区工作1个多月左右,杭州淳安人小黄(化名),因为贩毒被判死刑。这是钱锦标进入看守所工作以来,第一次和死刑犯打交道。
“去接待室,等待和他家人见最后一面时,是我陪他去的。从监区到接待室,150多米的路,他戴着脚铐,走了足足有三、五分钟。”小黄也许已经料到家人不会来,特意走得很慢。
接待室里空无一人,只有钱锦标陪着他静静地坐着。
“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,因为这是走向死亡的倒计时。会面时间结束,他最终没有等到他的家人。他们首先自我抛弃,所以才被人抛弃,眼角的底色都是绝望。”
那天之后,钱锦标本想回家和妻子、女儿说一下自己工作的情况,但总是话到嘴边,犹豫了犹豫,但还是没说出口。在他的眼中,和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,都是他在上完一天班后,离开高墙大院之后最想拥抱的美好。
钱锦标家住滨江,离看守所差不多40公里。通常,6点左右就要从家出发,乘地铁,换公交,等下班时,钱锦标有时要先去跑步,一方面,人到中年,在警察的岗位上也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体能,一方面,也是为了能把白天经历的这些五味杂陈,统统忘掉,再披着月色回家。
“我想,男子汉就是要干好工作,别让家人担心。”钱锦标说:“看守所里的这些在押人员也是有家人的,他们中的大部分,讲到过去,不会说对不起自己,但都会说对不起家人。”
而正因眷恋家庭,在艾滋病监管区工作6年了,这个秘密,钱锦标对所有人守口如瓶。
无法诉说的苦
钱锦标和妻子汪长菊,是相亲认识的。
“第一次见面,觉得他又黑又瘦,个子也不高,就想算了吧。但他一直没放弃,给我写了两年的信,再加上那个年代,姑娘都崇拜军人,我就嫁给了她。”
汪长菊说,“这么多年,我们全家都是围着他的。我父亲去世那年,我要回老家淳安陪母亲,考虑到转车不方便,让她带一下女儿。
结果除夕夜里,他还是代替别人值班,把女儿带到看守所去过年,他陪犯人看春晚,女儿一个人在他宿舍。”
汪长菊的工作是在杭州一家工疗站,她和同事要照顾37位有智力缺陷的成年人。妻子的工作总是让钱锦标忧心忡忡,因为他怕妻子受委屈。
事实上,汪长菊确实也被打过耳光。“他们大多时候都很好的,但有时候一旦情绪不对,会难以控制,会追过来,一定要打到你,一下子打到我眼睛上,忍不住就哭了。”但是,汪长菊不敢告诉钱锦标。就像钱锦标只告诉妻子,自己监管的区域是老弱病残,并不是艾滋病专属监管区。
这也许就是中年夫妻让爱呼吸的方式,只是不想让对方担心。

钱锦标多年来记下的工作日记
汪长菊回家会问老钱,“犯人会不会有人打你?”老钱都是轻松地说:“怎么可能?犯人怎么可能打警察?”汪长菊还是会问:“有没有特别难管理的?一个都没遇见过么?”
老钱说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脾气的,你要先熟悉对方。心里不要有忌讳,不能冷漠,也不能歧视,偶尔,可以鼓励性地拍拍他们的肩膀。”
但是,钱锦标绝对不会告诉汪长菊,这些经验,是他在工作中逐步体会到的。
新冠疫情期间,汪长菊从年初二就开始上班了,在看守所连续值班,一离开家就是40天。家里浴室灯泡坏了,五金店都在关门,网上购物也不发货,汪长菊骑着自行车,往返20多里,才买到灯泡,回来以后,钱锦标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妻子总是抱怨他不说话,连散步都是一前一后“像去拉练”。那个隐秘的世界积淀的所有苦闷,钱锦标不能说,不会说,“身体上的苦,过去就过去了,你说父母亲生病住院时,没法赶回身边,那心里叫不叫苦?但更苦的苦,是说不出来的。”
去年12月,杭州市看守所举办警民开放日,有媒体做了报道。没多久,钱锦标收到一封来信,是他监区之前的在押人员。
信里写:“钱管理,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相片,虽然您的身影被模糊了,但还是一眼认出您,看到您还是这么精神,真为您高兴。”
版权声明
1. 未经《新西兰天维网》书面许可,对于《新西兰天维网》拥有版权、编译和/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任何内容,任何人不得复制、转载、摘编或在非《新西兰天维网》所属的服务器上做镜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使用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2. 在《新西兰天维网》上转载的新闻,版权归新闻原信源所有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。
- 俄全女性战舰首次出海巡逻!隶属黑海舰队,演练应对敌方入侵
- 乐视网退市!半个娱乐圈和28万股民,因贾跃亭梦想窒息
- 珠宝店快倒闭,老板:700万的宝物谁找到就归谁
- 长江上的观音阁:洪流难撼“阁坚强”
- IS 圣战新娘被判回国,150 名恐怖分子紧随其后...
- 澳洲日涨近300例!美国小伙隐瞒病情害全家4口进ICU
- 3天确认关系!70岁老伯遇"真爱" 聊天截图辣眼睛
- 快讯!英媒:英国暂停与香港间的引渡条约
- 发生了什么?伊朗一夜之间确诊到2500万 远超美国
- 和新垣结衣一起惹哭全亚洲的三浦春马,上吊身亡了…
查看所有评论 共( 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