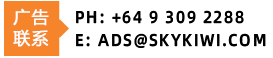在新西兰成为疑似病例会经历什么?一位妈妈全程记录
作者: Emma 日期:2020-03-06 16:46 阅读: 来源:天维网援引NZHerald
【天维网援引NZHerald消息 Emma编译】叙述人自述:“我选择不透露自己、孩子、医院和我所在的地方。这不光是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,也是为了保护与我们打交道的医生、护士和公共卫生官员的隐私。这对所有人来说,都是全新的领域。很显然,应对新冠肺炎的举措是严谨而复杂的。我也有不希望在社区内散播恐惧。以下是我的故事——”
周五晚上,女儿开始头疼。一夜之后,开始发烧。
我一晚没睡,听着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胸腔里的杂音,越来越焦虑。
我们是11天前从日本回来的,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给了卫生专线。
以为护士通过电话评估了她的情况,然后告诉我要送女儿去看医生。
我们2月中旬从日本回来的时候,新西兰还没有任何关于日本的限制。后来日本成为二类关注国家,我们也在需要14天隔离,并汇报病症的范围内。
周末的时候,我们的GP关门歇业了。所以我只得把两个孩子塞进车里,去当地还开着的急诊。
急诊的门上贴着一张标识,写着如果最近从海外回来,请不要进入。于是我带着孩子回到车上,给急诊的前台打了电话。
前台将我转接给了一位医生。医生说要上报给卫生部的首席医疗官,让我等5到10分钟。
一个小时后,医生走出来,说需要保持1.5米的距离。她指引我们去了最近的医院,并递给三个口罩,还按照我的要求给了我呕吐袋,因为我女儿觉得想吐。
就这样,我们开启了四天的隔离,开始坐立难安地等待新冠检测结果。
我们三个人被告知不要直接走进医院,而是把车停在下客区,戴上口罩,然后透过车窗向医院里的急诊员工招手致意。
问题是,没人看到我们,然后我们又打电话给那位送我们口罩的医生,最后才有人来接我们。
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走向我们的车,叫我们下车,然后带我们穿过几重门才进入隔离病房,然后护士去了隔壁房间。我们能透过玻璃窗看到、听到她和另一位护士讨论防护设备。
他们好像是也是第一次遇到潜在的新冠患者。
其中一位护士离开了那个房间。另一位留在原地的护士开始戴口罩,穿防护服,试戴了一下塑料面罩,后来又加了一副护目镜。
后来,她走进了我们房间,头上和脚上都没有戴防护设备,后来听卫生部说这些都是不需要的。
就我个人来说,我不太懂为什么不把头和脚的防护也纳入其中。就算让医生和护士安心也是好的。
我知道护士没有脚部防护还是有点不安的,是她亲口直接告诉我的,后来医生进来的时候也提到防护不够,所以只能自己穿上工业胶靴。
光看其他国家的照片,就知道新冠一线的人是全副武装的。一位在美国的新冠患者说,自己所在的医院里,护士直接用胶带把口罩与头部防护设备粘起来了。
我不是什么微生物学家,但要是病毒能附着在表面,那么头发、耳朵、鞋子等易感染的地方,只要触摸不就可能导致感染吗?
隔离病房小而朴素,天花板上有个通风扇。

Doug Sherring
“是什么声音?”我女儿问道。
“我觉得是负压系统在吸走细菌,”我跟她说。那时我还在想,护士已经做完了初步评估,我们需要在这个幽闭的空间里待多久。
之后,医生走进来开始问问题,然后又走了。走之前,他说要咨询传染病专家,看看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检测。
我们又继续等待,戴了口罩之后,我们的脸又热又痒。
后来,护士又回来了,说已经有了方案——只有我女儿需要接受检测,因为只有她一人有症状,而且还是轻症。
当时,我女儿登记的症状还是低烧,而且的胸腔回音是清晰的。
护士说,需要做三个咽拭子检测,两个是鼻腔取样,一个是喉咙取样。
左鼻孔取样时,我女儿又踢又弹,像一只惊慌的小动物。她留着眼泪说痛,但医生很耐心也很好,哄了一会儿,终于取完样了。
他们说要第二天才知道检测结果,我们要直接回家,并且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,不能离开家门。
我们心慌慌地穿过城里回家,心知不能停车买咖啡或牛奶。
我一到家就接到了电话,说我女儿现在被当做新冠疑似病例。根据卫生法案,我们要被强制隔离。
卫生官员反复申明,我们不能离开家,也不能让别人进家门。他还说,不遵守的话将会被惩罚,但我们可以去自家院子里。
我跟孩子们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——一个人在自己的公寓里,用两把椅子设置了一个跑道,跑了50公里。第二天早上,我儿子下了一个app,记录自己散的步——在12米宽的草坪上,他慢跑了2公里。
当他姐姐给他递水时,他打翻了水杯,我当时还笑了起来。后来,我突然开始担心是否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我不想让邻居来问,为什么我儿子在跑圈。我担心邻居们会开始担心同构空气传播感染上病毒。
于是我们进屋玩了一把大富翁,又看了会儿Netflix。
未知的检测结果一直悬在我头上。周日下午发现我女儿做的检测结果为阴性,但这个是检测感冒、流感和其他常见呼吸道病症的,我越来越焦虑。
一开始,她的轻症并没让医院有多紧张,所以我还是希望她没有新冠病毒,但我现在必须要接受她携带了病毒的可能性。
然后更糟糕的是,我们要等到至少会走一中午才能知道下一步的检测结果。
周日一晚上我都没合眼,听着女儿睡在身旁沉沉的呼吸声,我不禁在脑中一遍遍地设想各种情况。
如果她的检测结果为阳性,说是要立马开始追踪接触者。这可能意味着她就读的学校要关闭两周。
卫生官员还警示我,到时候可能出现媒体疯狂曝光,就在那个时候我哽咽了。
我躺着睡不着,不禁想着,如果学校要关闭,那么家长们得多生气。我当时满心都是恐惧。
我想着,我们一家三口将成为排外和恐怖情绪的靶子。一想到我带孩子出国滑雪竟然让一个社区都有了风险,我心里觉得更沉重了。
作为一个前记者,我知道媒体要找到我们是毫无问题的——只需要在校门口随便问几个问题,我女儿的名字就能被问出来。
我甚至开始想到,如果我的女儿成为新西兰第一个确诊的小孩,那么将会有多少标签被贴在她身上。
就因为她小小年纪,所以一切都将被放大。压力越来越大,我都感到胸口疼了,我还想着自己会不会也病了。
我知道孩子的父亲也将承受这些负担——我们2月7日去日本之前,他已经表达过自己的顾虑,因此我觉得更内疚了。
我计划了一年,出发之前还打给了保险公司。保险公司说如果取消的话,不会赔付。
那是,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世卫组织都没对日本发出任何旅行警示,而钻石公主号也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。
于是,跟前夫聊过之后,我们一致同意可以带孩子去——后来都很后悔这个决定。
周一最终还是来了,但检测结果却并没如期而至。
下午我接到了电话,是另一位卫生官员打来的,说样本还没送到实验室,因为在取样的医院,送样本的特殊次日达快递周末不上班。
我只想尖叫:“WTF?你们说周日,然后是周一,现在要到周二吗?”
但我并没说出口,我只问了一句:“那你知道这样等待下去给我的神经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?”
我被告知,之所以会延迟,是因为只有普通的病毒筛查失败之后,才会触发新冠检测。
这是我之前不知道,所以我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不满。
周一晚上,我觉得女儿99%的可能不是新冠病毒。
她退烧了,笑得很开心,还在走廊里跟弟弟玩起了曲棍球。我当时想着,及时检测结果为阳性,那我们也很幸运她只是轻症,希望她能有免疫力。
我感到松了口气,就睡着了。
周二迷迷糊糊就过去了,下午3:30的时候,我已经忍不住了,便给之前留给我的卫生官员的电话发了信息,接着一位护士回电称还没有结果。
我叹了口气,想着可能还得再隔离几天。不过几分钟之后,电话响了。
还是那位护士。
“好消息,”她说,“你女儿的新冠检测是阴性。你可以照常生活了。”
听到这个好消息,我们出门骑车、吃冰激凌庆祝,在街上为重获自由而撒欢。
我看着两个孩子在公园的秋千上开心地玩耍,但一个不好的念头又上了心头——我们家是躲过了成为第一个将病毒传到学校的家庭,但另一个家庭又能躲多久?
新冠肺炎到底会让世界变成什么样,还会继续多久?
扫二维码看更多精彩新闻

版权声明
1. 未经《新西兰天维网》书面许可,对于《新西兰天维网》拥有版权、编译和/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任何内容,任何人不得复制、转载、摘编或在非《新西兰天维网》所属的服务器上做镜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使用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2. 在《新西兰天维网》上转载的新闻,版权归新闻原信源所有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。
- 国家党炮轰:正是政府反应的不及时,造成了抢购和恐慌!
- 受新冠疫情影响,新西兰这种常见药品处方开剂即将限量
- 卫生专家:新西兰必须借鉴中国防疫模式 严控疫情
- 担心新冠病毒传播 毛利部落暂时禁止碰鼻礼
- 疫情正在发展中,而新西兰的学校们又陷入新困境…
- 总理Ardern发长文回应质疑:自我隔离确实有效!
- 梅西大学澄清:第二例确诊患者非本校员工
- 政府帮扶旅游业,有人认为“领福利”不如“保工作”
- 1名Kiwi高烧不退被困缅甸,医院员工善意为他买KFC
- 枪支改革陷入死循环,无法赶在恐袭案1周年际出台
查看所有评论 共( 条)